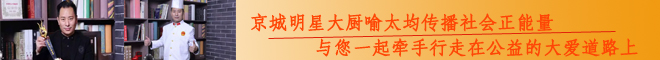|
说起湟中县李家山,就不得不提及卡约村。数次与友人走近卡约村,感受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原生态的文化。每当走进村庄,聆听着浓郁乡音讲述古村落及古羌人的故事,我的心常常怦然而动,有一种想顺着这条原生态文化走下去的冲动,去触摸卡约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含蕴隽永。 01 卡约文化是青海境内的一支土著青铜文化,因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于湟中县云谷川卡约村考察时发现而得名。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正因“卡约文化的首发地”而声名鹊起。 “卡约”为藏语地名,意为山口前的平地。过去它被列入“寺洼文化”系统,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把它与寺洼文化分开,命名为“卡约文化”(原称卡窑文化),理由是寺洼文化与卡约文化在地理分布与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分布区域和文化特点。 卡约村遗址面积较大,除包括整个村庄外,还延伸到村北耕地,1958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卡约村遗址不但是卡约文化的命名地,也是云谷川卡约文化遗存密集地,是卡约人聚集地之一。 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而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 自安特生博士发现卡约村遗址以来,卡约文化各个类型的遗址在安特生的发现中,从隐匿的地下状态逐渐揭开,也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世人。 近百年来,卡约村一直成为云谷川的骄傲。每次去卡约村,我与友人常常登上村庄西面的山脊眺望,只见洁白的秋云在潘家梁缭绕,一只山鹰穿过云层,向着绿肥红瘦的村野盘旋而下;云谷川,那片肥沃开阔的大川,一片片不规则的田地分布在山坡、平川之间,在树木掩映的村舍间,显得那么耀眼。 “何处寄乡愁,天涯聚乱流”。每次与卡约村有着渊源的林兆寿先生谈及卡约文化,自豪、无奈诸多感情书写在林先生的脸上。“我心中始终有一夙愿,沿着安特生博士走过的路走下去,成立卡约文化研究会和卡约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进而助推有关部门挖掘卡约文化,让我们的卡约文化走进世人心中。”在林先生的内心深处,卡约情,似大海波涛,似万千落叶,正恣凝愁,这一抹最纯粹最浓郁的闲愁嵌入他的心坎。 或许,对于林先生,对于情系卡约村卡约文化的谢佐、赵宗福、沈桐清(已故)等专家学者,沿着云谷川河、湟水河,成为一个历史追踪者,这一切或许是前定的安排。对于安特生,一个人类历史的伟大的发现者,那时一切还处于混沌未知的状态,而河流就是他唯一的方向。 倘若没有黄河、湟水河、没有云谷川河的指引,要在大西北的沟壑坡坎间找到一块距今3000年左右,甚至更久远的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将是一件极为渺茫的事。卡约村便是这渺茫中的一个渺小存在,在中国政区地图上,哪怕你用高倍望远镜也难以找到这个比针鼻子还小的地方,但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它却是黄河上游流域最显赫的标志之一,而第一个发现此标志者就是瑞典学者安特生。 岁月流逝,但人类生存之象——勤劳、丰盈、宁静,始终存留在卡约村人的生活中。 看今日的卡约文化、卡约村,不是看一个消失了几千年的标本,而是看一个活了几千年的文化生命。 在紧靠柏油马路边的“卡约文化展示厅”中,陈列着一件件出土文物,四面墙壁上呈现着一幅幅画面,全面有序地反映了远古卡约人的生活、祭祀、习俗、房舍等情景,目睹此景,使我不由想起“湟中昔赵侯,遗泽遍行潦”“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的句章来。 在展厅前的广场边,一把陶制酒壶正往一只倒唢呐状的陶杯斟酒的造型最为显眼,寓意着卡约人的热情与好客。在一侧,一个三角的陶鬲昂然挺立,似乎讲述着3000多年前的故事。 这个陶鬲是仿照1984年湟中县发现的那件素面陶鬲而制成。它侈口、高档、单耳、柱状足。据记载,陶鬲始见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是陕西客省庄文化数量最多的一种炊器,到商周时成为最典型的器物,青铜出现后,还出现了铜鬲,至春秋战国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鬲作为盛食器中最具特点的器物,成为中原地区礼制系统的重要礼器,随着商周文化向外辐射,其周边地区也相继出现。 据考古专家发现,卡约村因为有青铜器出土,说明这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据放射性碳14测定,卡约文化距今3000多年左右,相当于我国中原的西周时期。 通过卡约村古文化遗存的发掘看出,在青铜器时期,古代先民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那时,农业和畜牧业并重,这成为卡约文化鲜明的经济特点。 此特点还决定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在四五千年前,我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是迄今为止最早活动在湟中地区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是古羌人文化。 据《通典·州郡·鄯州》条注记载: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地。所谓湟中地,整体上指的是黄河与湟水相交的广大地区。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耕;兼之森林繁茂,草木丰美,是理想的畜牧环境。 在河湟谷地的众多文化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豆、小麦等农作物的遗迹,而且在民和喇家遗址发现了“世界第一碗面条”。这就说明早期人类社会像柔弱的婴孩,本能地寻找温厚的臂弯和富有营养的乳汁。而河湟谷地这方五谷丰登的土地,的确是一片可繁衍生息的乐土。 自那时起,古西羌人自学习了爰剑从秦国学来的种田和养蓄的先进技术后,其生活方式从单一的畜牧业过渡为兼农、牧和渔猎并存的方式。 而《说文解字》讲“羌”为“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检论.序种姓》中也指出:羌者,姜也。“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系象形字,画的是大头、盘角、大眼、小尾巴的“羊”字,如殷墟甲骨文就有“羊”字,显然是古羌人崇拜的“羱羝”(即盘羊),后引申为山神,作为图腾崇拜,至今,羌藏语系中作为“年神”,诸如年保玉则、年钦唐拉等。 关于卡约人随葬羊随牛的习俗,在其墓葬及典籍中得以体现——“冉駹夷出旄牛,重千斤,毛可为旄……”(《后汉书》)。在湟源大华乡出土的鸠首牛犬铜杖首;上孙家寨有墓葬在二层台南部两侧置有牛头、蹄、牛尾骨……有的墓中四牛蹄加以牛尾;李家山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村北部)、大通黄家寨及循化阿哈特拉等墓地中都发现用羊来殉葬。尤其是阿哈特拉山普遍以羊作为陪葬品,有的多达2000只,而有的墓中随葬羊角100多个,但多以某一段肢体,而很少用整只羊。只在李家山潘家梁墓地发现一例用整只羊来随葬。循化阿哈特拉的墓葬流行随葬羊角,并以此作为财富的象征。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还有大量的有关鹿、大角羊等动物题材的纹饰,这与羌族从古到对羊的图腾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羌人与羊的关系极为密切,也说明河湟古羌人逐渐走向较发达的畜牧业文明是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他们长时间驯化并圈养的绵羊,为他们解决的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还有防御寒冷的衣着问题…… 站在卡约村对面的山梁上,感受着暖暖的阳光,思绪穿越时光隧道,不由想起《周易·丰卦》“日中见斗,日中见沫”的记载及“日中有乌”的神话意象。卡约人和马家窑人、辛店人等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太阳崇拜贯穿了其生活的各个角落。记得在大通和湟源两县出土了两件卡约时期的鸟形铜铃,其形象真,腹内有一丸,摇之有声,富有阳刚之霸气。上孙家寨出土一件卡约青铜器牌饰,其中一面构图,布有五只一排的鸟纹。化隆上半主洼出土的饰鹰纹的彩陶罐上孙家寨出土的飞鹰骨管及蛇鹰结合骨管……经专家分析,太阳崇拜观念在卡约先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已是不辩的事实。 徜徉在卡约村,我要仰天追问的话题有很多很多,但站在卡约村对面的山顶俯视云谷川河穿越而过的大川,所有的问题都好像落在了黄河、湟水河及云谷川河水的漩涡里了,又好像刻在层层盘升在山坡上的梯田及河谷星罗棋布的农田书页之上了。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其实,久远的天问,从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就开始了。 于是,就在那时,黄河、湟水河与远古文明、河流生态的命题,时时萦绕在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的的脑海中。 在早期,对于黄河这样一条大河的干流,由于经常性发洪水,所以,早期的人类文化是无法利用的。只有诸如湟水河、渭河流域、汾河流域等这些黄河的支流,成为黄河文化的密码,中华文明也就从小何走向大河的,进而使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 湟水河,这条西宁的母亲河,不仅是黄河的支流之一,而且在浇灌“河湟谷地”这片肥沃土地的同时,也孕育出的河湟文化,也为黄河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营养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湟水河流经河湟谷地时,也就孕育出了这里独居特色的远古文明与生态文化——牛、羊、犬等动物,最终成为卡约人长期饲养的动物,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及精神需求,成就了卡约文化中的动物造型艺术——鹿纹、鹰纹彩陶罐、蛇鹰骨管、鸟形铜铃、犬戏牛鸠首权杖…… 每一种古老的文化或文明都会彰显自己的特征。从出土文物及墓葬可看出,卡约文化分布之广、陶器以夹砂粗红陶和灰陶为主,且素面陶为大宗,彩陶比例较小,多黑彩,施彩较厚的特征较为明显。透过这些出土的陶器,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史前的工匠,他们不知熬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心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这样一件件元气贯注、血肉滚烫的陶器。时隔3000多年,他们的生命依然是活生生的,成为我们解读远古生活及文化的解码器……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自安特生博士发现卡约文化以来,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地处青藏高原的河湟谷地,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浩劫与痛楚,卡约文化虽声名远播,但国内一直缺乏保护。 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在1978年前后的几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卡约村及与卡约村毗邻的新添堡、王家堡、包家庄、下西河、下坪等村庄相继挖出“坛坛罐罐、锈铁烂铜”的事情还依然清晰地流在老人们的心中。历时三个多月的挖掘,发现了古羌人居住的遗址和墓葬,运走了一箱箱文物后,就简单地回填了坑道,致使遗址遭到破坏。为了保护卡约文化遗址,1981年前后,青海文物部门抢救性发掘过一次…… 就这样,这个古村落,一个让世人骄傲的古文化遗址,在历史的长河里,微笑着、快乐着,苦涩着,渴望着…… 不论怎样,它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接通了血脉,成了一条青藏高原由坚石造就的文化命脉。 在走访中,一位70多岁的林姓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前后经过了两次发掘,出土文物除罐、鬲、瓮等陶器外,还有大量石制的刀、斧、臼、锤等,骨制的针、铲、锥,铜制的镰、镜、刀等,此外,还发现粮食(豆、麦)碳化物和较多的马、牛、羊、狗等家畜骨骼。 面对洪荒,古羌人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对生态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局限,促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念的形成,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站在21世纪的阳光下,我们守望卡约文化,仿佛自己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因为,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仍然与传承文明传承文化有关,而且,所面临的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建设新青海,建设幸福家园。 “假如像海东市乐都的柳湾一样,将遗址和文物保存下来,那一定是一处很吸引人的‘卡约文化’旅游招牌……”曾多次,林兆寿先生感慨万千。也曾多次,我在晚风中,在清冷的月光下,感受着林先生的伤痛与渴望。 02 历史,总是在民间的记忆中静静地流淌。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社会的变迁就是一条“生态”的迁徙。 要了解河湟文化,不能不了解黄河与湟水河。为了探寻我憧憬已久的卡约文化遗址,今年8月中旬,我与友人再度踏进卡约村,一路追着安特生博士的踪迹,走近了云谷川河。愈是深入,愈是明白,这条湟水河的支流——云谷川河,是一条绝对不可忽视的河流。 卡约村所属地李家山镇,地属整个云谷川,著名的湟水河支流云谷川河穿越此地。当湟水河流经湟中境内时,湟水河六条大川相沟通,成为西三川(云谷川、西纳川、甘河滩)、东三川(北川、东川、南川)。而云谷川河则发源于金娥山,上游分为东西两河,两河间是一座北高南低鱼脊形的大缓坡川地,当地人俗称云谷川为鳌跌沟或双龙川。东西两河由北向南流至卡约村南汇成一河,卡约村坐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处。 云谷川河,这条湟水河的支流,一路走来,滋润出这里的农耕与游牧文明,也孕育出了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 黄河、湟水河,云谷川河……在她们的身边,历史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生活印痕的智慧之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原之中。 为了发掘中华大地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安特生博士全凭两条腿沿着湟水河、沿着黄河,在苍茫大地上行走,他在卡约村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瓷碎片(现如今,在卡约村的庄廓及周边断崖中,还时常挖出陶瓷碎片),这使他惊奇万分。因为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是人类发现仰韵文化、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铜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之后的一个新发现。 “终然浩劫入沧桑,纵有赤心天不惊”。虽然那时还没有发现有彩陶的卡约陶器,但这一发现让他再次震撼,就如卡约村民在自家庄廓或田地里挖出陶罐或捡拾到瓷片时那样,感到不可思议。可惜村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令人亢奋的文化发现,茫然而无知(就如林先生所述,孩提时,一件一片片铁片串连而成的盔甲,由于村民文物保护意识不强,见小孩们玩耍时动辄划破手脚,于是,被老人搭在墙头上,风吹日晒,最后不知归处。同时。村民们不知道这里埋了多少陶制品,反正在自家院子、田地里锄草、种植时,时不时就会翻出几片陶片或陶罐。那时老乡们叫它为“红泥罐罐”,可谁也不觉得它是文物,是宝贝。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就坛坛罐罐就是卡约陶罐)。可以想象,安特生博士当时的表情与心情——两腿发抖,惊讶得足以让自己下跪;当他抚摸着一件件陶瓷或一片片瓷片,似乎感觉到来自3000多年前的火焰,手心里一阵阵滚烫、战栗,他不敢相信,就在3000多年前,东方人就开始使用青铜器了。由于他的偏见、傲慢,他固执地提出了“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 就这样,一个埋葬了3000多年的文化遗存,一经发现,就让世人震惊。 安特生博士的这一发现,就是一个溯河而上或顺河而下的往复穿梭、踏勘寻觅的过程。 卡约文化是安特生博士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此发现,再一次将现代中国古史的视野再度拉进黄河大西北,很大程度改变了中原文化或中国主流文化的视野。由于马家窑、卡约文化的发现,吸引了顾颉刚、夏鼐等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光临青藏高原,纠正了安特生博士“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 继安特生博士于1923年发现卡约文化起,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专家在青海境内发现了1700余处卡约文化遗址,东起甘肃临夏地区与青海省的临界县,西至青海湖西岸到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北起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黄河沿岸皆有分布。而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遗址中,就会知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源头在哪里…… 考古专家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不同的墓葬及数量不同的随葬品,但墓葬及随葬品最为集中、最为密集的区域为湟水流域的青海境内黄河河曲地带及湟水中上游地区,尤其是湟源大华出土的两件“犬戏牛鸠首权杖”和34面铜镜文物(《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帝既与西王母会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虽月而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里才是西王母活动的中心地带,也印证了“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地”的条注,也说明了原始社会正逐步走向解体…… 自在卡约村发现其遗址的岁月中,卡约文化无彩陶的观点成为一种遗憾。 孰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宁古城台和湟中朱家寨遗址发现有卡约文化的彩陶器、陶鬲和铜戈、铜泡等,纠正了过去认为卡约文化无彩陶的观点。 此后,在湟源、大通宝库、东峡、尖扎、刚察等多处相继发现卡约文化遗址,一处处墓葬、一件件陶器的重见天日,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世人,一次了更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也引发了“生命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垄断…… 目睹了卡约文化陶器碎片,我竟然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幻觉,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卡约文化的念头愈发地强烈。 在翻阅史料中发现,“卡约文化”藏语为“卡窑文化”,“卡窑”,意为山口前的平地,而且“窑”从“穴”从“缶”,原指烧制陶瓷器和砖瓦的一种地下土灶,后来沿用为人类居住的“窑”。卡约(窑)村的“约”除烧制陶瓷土灶外,是否还指古羌人穴居建筑呢?在与林先生的聊天中中,陡然之间,这个大胆的猜想潜入笔者心头,且《黄帝内经》《韩非子.五蠹》等文献中的记载也浮出记忆:往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在走访中,同行的友人刘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带着疑问,我们两度走进河湟博物馆,走近四五千年前的河湟历史。 经过考察,发现卡约文化的聚落遗址多选在黄河和其支流河谷两岸的台地上,房址结构有半地式和地面起建两种。选在河流两岸地势较高的台地上,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取水方便和预防洪水;或健在高山或地势险要的地方以预防其他部族入侵。譬如,湟源约洛石崖、莫布拉和尖扎鲍家藏遗址,房址分单问双问,周围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形制窖穴。而且,为了使房屋内的地面坚固耐用,人们换在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红胶泥。但其制陶业与其他文化遗存相比,不甚发达。在潘家梁墓地男性随葬品除陶器外,主要是铜镞、斧、戈、刀等,女性随葬品主要是骨锥、针、管等纺织工具。 这很明显反映,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古羌人男女有明确分工,男子在外进行农牧或狩猎等活动,女子主要在内进行农牧和纺织业等劳动。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卡约时期的气候条件、水文环境、农业生产、建筑建材及文化理念…… 虽说河湟谷地地处青藏高原,但大部分地方被黄土所覆盖。而且黄土的一些特性帮了古羌人的一个大忙。 在四千年前,河湟谷地已开始早期的农业生产。据史料记载,在距今约1200~11000多年间,人类文明面临了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地球本来处于温暖的间冰期,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次急剧降温,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时间里,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于是植物大面积死亡,原有的很多动物也灭绝或向南迁徙,原始人类可以采集的果实和种子等食物,可捕猎到的猎物,都大量减少,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黄土高原、河湟谷地的人类只能另辟蹊径,人民开始驯化粟、黍,原始的旱作农业开始萌芽。而且在距今4000~3600年的时候,青海地区的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逐步掌握了简单的冶炼技术,冶炼出了红铜和青铜,这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生产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同时,黄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即“自肥性”。记得20世纪美国地质学家庞波里在考察过我国的黄土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就这样,河湟谷地就成了古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产生了马家窑、齐家、卡约、宗日及辛店等一系列文化。而卡约文化则是青海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 目睹着博物馆里来自河湟谷底的文物,浏览着书写古河湟生活的历史画卷,吮吸着来自四五千年前的河湟文化味道,脑海中不断浮现出3000多年前卡约人的生存图画来—— 在云谷川那片良田美池间,一座座方状半地穴形、圆状半地穴形或平地凸字形的屋子掩映林木间,屋舍旁,河水潺潺,在东西两座大山苍苍莽莽的原始森林中,芊芊苍苍的灌木间,莺歌燕语,鸟兽成群。就在这美丽迷人的“世外桃源”里,卡约人或种植,或放牧,或狩猎、或采集。闲暇之余,他们撞千年之钟,敲灵鼋之鼓,起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百人唱,千人和。千百年来,鸡黍桑麻,子子孙孙,延绵不断…… 深入云谷川,深入卡约村。这里,一个风雨剥蚀的烽墩,一段夯土古城墙,村口一棵老柳树,乃至一瓣碎陶、一段锈骨、一个传说、一句俚语,都透着千年的沧桑、藏着深沉久远的底蕴,印着多数华夏儿女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的“靠天吃饭”的生存状态,刻着河湟谷地永不消失的文化符号,给了我们生存的基座、文化的基座。 站在卡约村西面的山脊上,望着不远处白云缭绕的潘家梁,我陷入了茫然,环顾四周,这片从史前绵亘而来的云谷川,被苍苍郁郁的树木、庄稼所覆盖,在一座座漂亮大器的农家庄廓的点缀下,讲述着3000多年的前古羌人的勤劳与智慧,讲述着西王母自瑶池沐浴而出,蹁跹东巡余昆仑故土及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的神奇故事。 在林先生的叙述及文献记载中,一个史前的村落渐渐露出了清晰的轮廓。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站在卡约村对面的山脊上,远眺着这个水汽氤氲、生机盎然的云谷川,俯瞰着这个3000多年前的原始村落,那些在邈远岁月中难辨面目的古人,在云谷川春种秋收,生儿养女,生老病死,他们曾经的一切,又与今人何异?甚至觉得,远古的这个原始村落,比今天的现代新农村更充满了世俗的热闹。至少,他们不会像如今的村民那样四处打拼务工,一村人,一家人,从生到死都厮守在一起。团聚在一起。 望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河水,一看就知道逐水而居是他们生存生活的选择,山下是东西两河,便于取水,便于灌溉田地。两岸是肥沃的土地,延绵的原始森林,宜于狩猎与种植。 在林兆寿家,我们见到了其年逾七旬母亲,闲聊间问了老人很多有关卡约村及卡约文化的事情,这位淳朴的老人将自己所知如数讲出。在讲述中,他指着离家不远的山梁说,虽然我们住在山脚下,但从未担心发生洪水,老一辈也未曾遇到过洪水淹没村庄的事情,原因是云谷川是双龙川,川里有东西两条河,夏天再大的雨水也只是顺着这两条河往下面淌,最后淌到湟水河,根本淹不到我们的村子…… 怪不得古羌人要选择云谷川这条风水宝地,源自在于“双龙保佑”因素,这就应和了古人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此喻卡约村,恰如其分。 在村畔,一座较有规模的砖厂正在运转,我随意抓起一撮土,在使劲揉搓中发现,这里的泥土不像其他地方那种松散的黄土,而是粘性很强的红胶泥。由于前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雨,不知不觉间鞋底粘了一层厚厚的红胶泥,进而使平日显得轻柔的鞋显得那么沉重,不得已用木棍不断剔去随剔随粘附于鞋底的红泥巴。没错,这就是黏土,是古人用来制造陶器的陶土。由于东西两座山上都是这种黏土,也就不用担心这里会发生山洪暴发或泥石流之类的天灾。 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卡约古村落在历史的框架里形成了一个有呼吸、有年岁、有传承的文化要地。几千年来,古羌人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游牧耕种。他们,在这里演绎着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爝火,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传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虽然昔时的云烟不复存在,但在波光闪亮的河水里,在北高南低鱼脊形的大缓坡川里,依稀看出人类从史前以来安身立命的处境,依稀看出赵充国屯田时粮草充盈的辉煌。 面对卡约村“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几千年前游农牧时代的文化遗址,人类的艺术珍品,想到 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怎能不使河湟民众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为之惊奇、为之庆幸、为之振奋! 时光易逝,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卡约文化闪耀着圣洁的光芒,成为大美青海一处绝佳的古文化精神遗址,它将会向世人洞开一个又一个地表深处的秘密,传唱那千年不朽的神秘故事。 王祥奎,70年代出生在青海,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散文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苑散文网签约作家,散文诗词散见于《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西海都市报》、《海东时报》、《中华诗词》、《作家选刊》、《雪莲》等诸多报刊杂志,数十篇人物通讯发表于《青海日报》,数十篇散文在省内外征文比赛中获奖,其中《又是一季雪花飞舞时》、《贵德行吟》在《2015年中外散文诗歌邀请赛》、《第四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中获得一等奖。 |